胡复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正式向全日本发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战败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战败为标志胜利结束。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拟制好的《战后复员计划纲要》,全国在战时西迁、南迁到大后方国统区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机构开始准备复员回到战前原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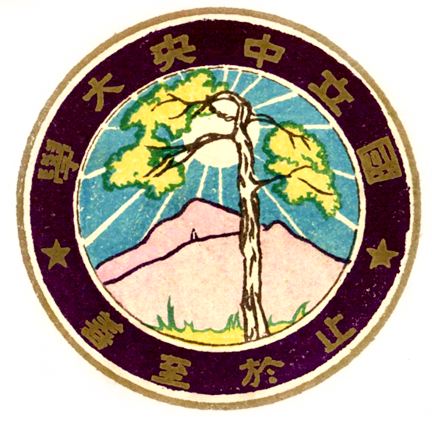

国立中央大学在不同时期的校徽
国立中央大学于八年前西迁重庆,胜利后,中大成立了复员委员会,由刚到任不久的吴有训校长兼任主任。体育系主任(前总务长)江良规、胡家健任复员委员会副主任。复员委员会下设:调查委员会、校产清理委员会、接收敌伪物资调查委员会、教授宿舍建筑委员会,重庆成立中央大学留渝办事处,江良规兼任交通组主任,主持重庆方面的复员安排。胡家健、王书林主持南京方面校产的接受和修缮。化学系章涛教授任复员委员会秘书,处理日常会务并协调各方面工作。考虑到长江三峡水流急、暗礁多,抗战中被日军炸沉的船只还没有清理。加之川江轮船吨位大小不一,各船上下行不能夜航运行,有些必须在宜昌、汉口换船,和战前学校西迁时一样,中大在武汉设立汉口办事处。由徐仲年任汉口办事处主任,周名章任宜昌办事处主任,负责部分需要在汉口、宜昌中转的善后工作。各办事处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由组长自行组织,各人照支原薪并无津贴,部分学生也参加了复员工作的事务。
复员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接收委员会,下设建筑委员会、教职员宿舍管理委员会、校具保管委员会、丁家桥校区接收建设委员会等。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校长吴有训兼任,副主任委员由工学院院长、土木工程专家卢恩绪担任,委员有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农学院院长冯泽芳、文学院院长何兆清等,接收委员会另聘专职秘书、文书、收发、技术员、事务员、统计兼书记等九位职员。十月份起,卢恩绪和几位委员先后乘机到达南京组织接收校产。
抗战前的一九三七年,中大教师为29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33人,讲师34人,助教123人。复员时的中大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教师人数已经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于讲师)38人,加上职员共1251人。规模之大,院系之多,在当时的大学中遥遥领先。
抗战时期中大师资队伍的有力充实,不仅为数量的增多,也是质量的提高,一大批有名望的学者集聚于中大旗帜之下。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专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憨廉、阴毓章等。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战后国家建设的及时开展,中央设计局制定了各方面专家去欧洲和美国考察研究的计划。一九四四年八月,胡焕庸教授卸任教务长以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受教育部委派,胡焕庸教授就开始积极准备,利用一年的休假时间,去美国考察大学和进行研究。他没有参加国立中央大学的复员工作,在日本投降的次月就从重庆乘坐美国军用飞机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再转乘美国军用运输舰经印度洋大西洋去了美国考察研究。
十一月,吴有训校长亲自赴南京办理接收手续。中央大学原希望在一九四五年底第一批复员回南京,但是因水道拥塞,运输工具缺乏,特别是抗战期间南京中大校舍绝大部分被敌伪征用,损坏严重不能顺利接收使用,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初才进行。
经教育部核准,中央大学的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复员工作独立进行,他们得到四川省地方部门的大力协助,人员和图书仪器都先于重庆中央大学沙坪坝本部回到南京。
交通工具方面,原计划长江航运为主,但在四月初中央机关复员后内战爆发,军运占先,客货运均暂停。学校于是首先考虑到公路运输,由一些单身教职工组成包车,每两辆由川往陕、豫、皖返宁,每车40人,在途十余日。后因旅途生活艰苦而费用较高,因而未再组织。另有包机两架每架约25人多为单身教授,但因所带行李受限每人只20公斤,因而也未再组织,直至四月底在各方努力下,才有轮船可用。但中央大学复员航运所获份额在川江所有运能中虽然已占1/4,每次也不过百余人。复员工作极为迟缓,经再三努力,才在重庆行营会议决定运力中占1/3。
中大复员委员会当时有一专人每日跑运输管理处了解川江中各轮船吨位及航行情况。那时川江不能夜航,而且受天气影响也大。所以每艘轮船夜宿何处、清早何时开行只有当天才能了解清楚。因此该专人每天8时左右就在管理处了解,以定何日何时可有多少票能走多少人,待一切均定下后才能购票,每票均需填有姓名并贴有照片。为此待人数确定后再回校决定可走师生落实到人,然后才能持银行本票购回船票,再将船票分发到人准时集中送上轮船,手续繁多。一般师生下午四时后可登船,待登轮后立即离岸,时间相当紧张,工作人员多在船离岸后才得以回校休息。因而办复员工作,每天工作紧张时间很长。
为了准备复员,中大在一九四五年秋就将学年缩短,加紧完成功课,全校教学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结束。经训导处和复员委员会调查,中大学生的复员人员,按学生志愿,分为自行返京、缓期返京及随校返京三类。凡自行返京者,发给旅费法币七万元,并预发五、六、七三个月的生活费用三万元。缓期返京者,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以前集中到重庆,由中大驻渝办事处分配船票东下。随校返京者,则依照年级系列,分批分组,每组各有领队,依次东下。
南京四牌楼中大校址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征用为陆军医院,胜利后,又被军事委员会接管改作伤兵医院,中央大学接收时仍有数百名伤兵未予搬出,而东南、中山两院又被借与航空委员会作为回国空军临时宿舍。丁家桥医学院校产被国防部联勤总司令部接收改为仓库和宿舍,共309亩含181户居民。三牌楼农学院校址被改为药厂、木工厂和仓库,部分校舍毁损严重,接收工作困难重重。经与多方交涉,接收工作延至次年二月。
接收委员会除组织接收、腾空校舍、安排教育部临时大学事务、寻找中大西迁前留下的器材、设备和书籍、将日军在战时征用的伤兵医院用地办理手续外,还配合教育部驻京沪区特派员蒋复璁,报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汪伪时期在南京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国立模范中学”校长的龙沐勋,因“接受伪令与敌伪合流且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嗣又鼓动风潮企图破坏接收工作”予以逮捕。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全校教学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结束。自五月起至七月末,国立中央大学在沙坪坝、华西坝、柏溪、青木关的全体师生,在非常艰难的交通条件下,以超过八年前西迁重庆三倍的12 , 000多名师生和家属,分八批乘船经宜昌、武汉从三千里外的重庆,唱着胜利的战歌回到南京四牌楼和丁家桥校区原址复校,其后陆续运回南京的还有部分仪器、设备、档案和专业书籍资料。这些胜利复员返回首都的师生,与八年前从南京西迁时一样,都只有随身的简单行李。中大西迁时,有2 , 008只箱内钉上铁皮的坚固木箱和各种包装物,装载了能带到重庆的全部教学用品和图书档案,前后六个月分十批才运到重庆。中大复员还都时,新订制了甲、乙、丙和特种规格四种1, 400木箱,实际使用的木箱和各种包装物有5 , 000件,才将学校常用的设备、书籍和物资等装箱运回南京。考虑到南京校舍学习用家具几乎一无所有,为了尽早安置好全体师生和开学,在重庆购置的双层睡床446张,改制方凳1800张,两抽屉桌1100张,办公桌222张,绘图板1200块,图书馆书架200余件也都陆续运回了南京。
个人方面,有部分在重庆期间成家的教师和当地教职员留在了重庆。八年来在重庆招募的技工860人给资遣散,余50人随校返回到南京。不仅校舍、医院、农场和用品、艺术品和部分文件档案、工具、各种仪器设备,包括西迁时历经千辛万苦带到重庆并培育的畜禽良种,八年来在重庆建设的一切几乎也都留下了。工学院航空系的教学设备大到战斗机一架,教练机三架、各种机床,风洞等模型也都留下了。这种物资设备的馈赠也是中大西迁时和重庆大学等方面的共识,即重庆方面支持中大西迁办学,中大复员时要将自用的校舍、物资设备留下,以支持西南大后方的教育事业。中大师生离开沙坪坝时,还将无法带走的部分书籍转赠给附近的各学校。不仅国立中央大学是这样,抗战时迁往大后方的所有学校几乎也都如此。这些训练有素的教职员和留下的物资设备校舍等,对战后西北西南等中国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庆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坝校舍由毗邻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龙坎校舍由重庆青民中学接管;医学院在成都开办的公立医院由四川省政府卫生实验处接收,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并留用医学院教授黄克雄担任院长。学校还在重庆设立留渝办事处,在武汉设立汉口办事处,专门负责处理善后工作。
和西迁重庆时最大不同的是,复员的队伍里,多了数十口棺木。八年抗战时间里中大在重庆去世的教师、学生和亲属,大都停灵在重庆。中大复员时,学校没有忘记这些与中大共患难中逝去的生命。学校和各界包租了民船,将这些棺木运往南京和其他集中地,继而运往逝者家乡安葬。运往江苏的棺木承运方是由无锡旅渝同乡会联系的,但是这部分灵柩较多偏重,租用的民船又过于破旧,下行到汉口时该船搁浅倾覆,部分棺木搁浅在江滩上。中大又派人紧急飞往武汉,代表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和中大驻武汉办事处一起,雇佣民工将棺木捞起,另外包租了民船才将这些棺木运到南京。
南京四牌楼中大校址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征用为医院,胜利后,又被军事委员会接管改作陆军医院,中央大学接收时仍有数百名伤兵未予搬出。经反复交涉,陆军医院仅交出东南院、中山院及南高院三座校舍,而其中的东南、中山两院,却已借给航空委员会作为回国空军临时宿舍,一时无法收回。几经交涉,始将附中校舍先全部收回,中大随即将附中教室加以修葺后充作学生临时宿舍和部分教职员暂住。即便是德高望重的教授,如果南京没有原住宅可以居住,到达南京后也只能先在教室中安家,有的甚至两家合住一教室。床铺方面,除将重庆带回的部分木质床铺安装启用外,其缺额不得不商借千张双人铁床应急。丁家桥医学院校产为国防部联勤总司令部接收改为仓库和宿舍,其面积共309亩含181户居民,经交涉和教育部协调,联勤司令部同意除交还原有校产外,又将原劝业会旧址及房产一并移交,以便中大用作扩充教学需要,该地块面积合计有800余亩,各式房屋100余栋,虽然破旧不堪但是可以救中大用房用地燃眉之急。三牌楼农学院校址被改为药厂、木工厂和仓库,部分校舍毁损严重,接收工作同样困难重重。后经与多方交涉,接收工作延至次年二月进行。
中大回到南京以后,没有一刻的喘息和修整,急迫面临的两个最主要问题就是校舍的修理扩建和一九四七年新学年的招生。战前的中央大学,学生只有1, 000余人,没有教职员宿舍,教职员大都不是居住在学校。战后复员回到南京的中大,仅学生就有4 , 586人,学生宿舍急需添加建造,一千多位教职员和家属的住宿问题同样急待解决。吴有训校长提出将农、工、医三个学院迁往丁家桥第二校部,文、理、法、师范四个学院留在四牌楼,以便于和不远的中央研究院加强合作。接收委员会先后购买了附近的四牌楼、兰园、成贤街、九华山、高楼门等处83亩土地,在成贤街东文昌桥原中大农场旧址临时加建七大栋二层学生宿舍、两座饭厅和百间活动房屋, 又在九华山修建了教授住宅,丁家桥、三牌楼两地兴建教学楼、图书馆、餐厅、运动场、学生宿舍及教授公寓。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由美国运送到中国的军用活动板房152栋,除分配医学院农学院及附中、附小30余栋为学生宿舍外,其余分别建于图书馆前、九华山及丁家桥等处。两层者为教授住宅,一层者为职员宿舍。与此同时,中大对原有的一些房屋也加紧修整。在校舍维修、安置高潮时,有1238名工人在同时赶工。学校也竭尽全力,将包括图书馆、体育馆、牙科楼,各种实验室等全部校舍都充作临时接待住宿之用。即便如此,中大的校舍依然紧张,不得不重新分配。原先位于文昌桥的学生宿舍,改变为教职员宿舍,农学院独有的丁家桥校舍,分离除部分给医学院使用,所有的学生只能八个人一间先住起来。
中大校舍的清理维修和建造过程,需要建筑方面的人才参加设计、监督施工。中大向各地的往届建筑、土木系毕业生发出呼吁,共征询到18人回归到母校短期服务。工作最紧张时,建筑土木系的助教和高材生10人也参加共事。
据复员委员会工程组的报告,在恢复校产各类房屋修缮期间,共修理及新建房屋134座,各类铁床、木器等家具16,560件,水电卫生设备购买维修等不计其数。其各种工程共计营造装修等总价为国币4,851,016,745元。
原先位于南京四牌楼的中大附中,抗战期间迁移到贵阳,中大又将重庆青木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改为中大附中青校,在沙坪坝又办了一个中学简称中大沙校。两个中大附中,合计拥有四十个班级。战前的南京大石桥校址只有五座楼房和一点平房,只能容纳十二个班。中大将此改建为中大学生宿舍。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工学院五院及农学院的一部分与附属医院设于四牌楼,称为中大第一部。医学院、农学院二院及一年级与先修班设在丁家桥,称为第二部。将中大附属中学也整体搬迁,设置在三牌楼战前农学院的旧址。附属小学分设大石桥、丁家桥两处,一设大石桥前实验学校旧址,一设丁家桥本部第二部内。七个学院、四十二个系科及研究所,规模之大仍为国内独步。
战前,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中华门外石子岗计划征购的8 , 000余亩土地,本拟重建中央大学新校区,后因抗战西迁而中止。已征购部分抗战期间当地农民300余户将其分割耕种,接收委员会虽已经向市政府申请军警支持清理,但是农民不配合难度极大。政府复员后百废待举教育经费有限,短时间内按原计划重建迁校已不可能。中央大学接收委员会决定在此建立“中华农村福利试验区”,由农经系主办。其中的800亩借与农林部中央畜牧试验所,用于和合办“石子岗森林畜牧试验场”,作为放牧之用。
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西迁以来,历经罗家伦、顾孟余、蒋中正、顾毓琇和吴有训五任校长,从南京西迁到西南大后方重庆。近九年后的一九四六年夏,中大师生唱着战歌,复员回到了他们昼思夜想的南京校园。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与中央大学在西迁重庆九年前的同一天,中大在南京宣布开学恢复了教学生活,实验中学也从贵阳复员回到南京三牌楼复学。达打打打达的打达打的……,上课的军号声从南京中大校园吹到了重庆沙坪坝,现在又重新回荡在复员后的南京四牌楼校园怀抱。之前多年冷冷清清的四牌楼校区四周,随着中大的复员,校园附近以中大生意为主的各种日用小商店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奇迹复苏,有名的松鹤楼、满庭芳等餐馆也如同九年前一样热闹非凡起来。战后的南京是长江南北花生米的集散地,“南京花生米”远近闻名,农民和小贩散布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同文昌桥学生宿舍区马路边的大小酒馆相辅相成。节假日和晚上,自修结束的同学和教授往往约上三二好友,一瓶啤酒,一碟花生和豆腐干,花费不多,海阔天空无所不聊。虽然生活清苦,但是能够如此放松战后还都的情绪,也算是苦中有乐了。
复员回到首都的中央大学,没有忘记校园西北角的六朝松。年代的刻痕,已经让年迈的六朝松成为空心的植物,要不是及时用水泥和钢骨填充和支撑,它再也不能伴随着中大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毕业。

国立中央大学的标志性校景六朝松,其历史已经有千年以上
复员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校方负责人是校长吴有训,教务长高济宇,训导长刘庆云、总务长贺状予。聘定的各院、系负责人如下:文学院院长楼光来、法学院院长何联奎、理学院院长孙光远、工学院院长陈章、农学院院长罗清生、师范学院院长罗廷光、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中文系主任伍俶、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历史系主任贺昌群、哲学系主任刘衡如、法律系主任何义均、政治系主任孙本文、数学系主任唐培经、物理系主任赵忠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气象系主任黄厦千、地质系主任张更、生物系主任欧阳翥、心理系主任肖孝嵘、化工系主任时钧、土木系主任沙玉清、机械系主任胡乾善、电机系主任陈章、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水利系主任须凯、建筑系主任刘敦桢、农艺系主任金善宝、农化系主任刘伊农、园艺系主任章守玉、森林系主任郑万钧、农经系主任吴文晖、教育系主任徐养秋、体育系主任江良规、艺术系主任吕斯百、牙科系主任欧阳官。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国立中央大学由校长负责综理校务,设校长办公室,协助校长处理日常事务,设主任秘书一名,可以代替校长行事。复员后,先后出任主任秘书的是彭百川、贺壮予、吴功贤等。教学与行政事务分别由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分管。先后出任教务长的是唐培经、高济宇、周鸿经、罗清生等;出任训导长的是沙学俊、刘庆云等;出任总务长的是江良规、贺壮予、戈定邦等。

国立中央大学校园西北角的梅庵
中大回到南京后的第一次招生,学校决定在八月下旬办理报名手续,九月五日和六日招生考试。学校将招生分为两个步骤。先招收各院系本科一年级新生和二年级以上的插班生,中大研究院和专科的招考放在大学部之后进行。报考地点分为七处,除南京四牌楼校部外,另委托代办者分别为:杭州浙江大学、北平清华大学、武汉武汉大学、重庆重庆大学、西安西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中大当年毕业学生800多人,退学、休学学生200多人,合计超过1000人。八年抗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各方面都相当热情,考生和录取的比例很难确定。学校决定新生的录取,不受名额限制,仅视投考学生的成绩确定。大致来说,文、理、法、农和师范五个学校各系组招收一班,约40人。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电机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四系和医学院的医本科招收双班,约80人。但这还不算是最后定案,最后录取的人数会根据考生成绩调整。此时的中央大学,经过八年抗战的辛苦耕耘和全社会支持,规模之大院系科组之多,远高于其他大学,已经是全国之冠。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内地沦陷区一一收复,战时西迁到大后方的学校既需要迁回,抗战期间辛苦建设的西南西北文化水平又必须保持,而经过八年沦陷区的学校及文化机关大都毁损严重需要尽快修复,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顾及到这些方面的维持是相当艰难的。战后的中国,物资缺乏、财政困难、生活费用高涨,原抗战期间实行的公费教育措施等战时救济办法,本应随战事的结束而停止。考虑到国民经济实际困难的情形,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批准,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公费制延长一年,至一九四七年暑期。即便如此,学生的餐食标准比之以往还是有明显下降,飞涨不已的物价,从教职员和学生们的脸上就可以很明显的一目了然。同学们用尽一切办法,寻找着各种有收入的兼职。女同学则组织了一个没有地点的工艺社,为人编制寒冬必不可少的毛衣。国立学校的公费生,分全公费和半公费。新学年招收的新生,其全公费和半公费名额分别从原先的40%降为30%(抗战从军的学生复学不受限制)。本次招生是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范围招生,不仅原战区和后方,收复区学生报名也相当踊跃。
功课方面,医、工、农三学院的功课较为繁重。医学院读五年,外加一年实习总共六年才能完成学业。学医的人都必须要忍耐和细心!中大医学院有其一贯作风,对于同学体格尤其注重。医学院的学生凡读过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时候,有严格的体格检查,不合标准的要受到休学、转院、退学的处分。工、农两学院的同学大致上午在课室听讲,下午在实验室、工厂、农场实习,晚间是赶习题,做报告的时候。图书馆的座位供不应求,沙坪坝上的茶馆,以往经常是一杯清茶,一把竹椅,用于学生悠闲时的放松和聊天,但是每逢考试前,早就坐满各系复习用功的学生。忙碌之余的同学,唯一的闲暇是在晚饭之后自修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会三五成群,到外面去散散心。从开学后第二个月开始,许多平时考试会接连起来,一直考到大考,。有些教授要赶课,喜欢拿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来举行考试,许多专门科目一考就考一个上午,下半天的时间纵使你一直躺在床上,也难恢复上午在考场上那种过渡紧张后的疲劳。
比较起宿舍的拥挤和餐食的低劣,复员后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座位偏少,从清晨起天天人满为患都是常态。唯一幸运的是位于成贤街的中央图书馆或者学校的大礼堂也向同学开放,这两处设施解决了中大学生的读书需要燃眉之急,也几乎天天爆满。
功课如此繁重,校方和同学们都一致确认“身体第一”。中大有一种很好的风气,上自教授下至工友都喜欢运动。体育系的教授就有胖子,长子和娘子军的球赛,别开生面。在沙坪坝,那样狭小的场地,三四个仅有的球场上,每日清晨,体育系有两位先生领着不少师生学太极拳,这是“志愿的功课”。教授不取薪俸,学生自由去受教。中大的普通体育非常严格,各年级各院系每周有二小时的体育课,跑步、体操,十分认真,上课下课都要点名,没有人敢偷懒。学期结束时逐项考试,如果不及格,第二个学期多加两小时的体育,算是辅修,仍需及格。否则一直拖到毕业,也有因为体育没有修及格而不能拿毕业文凭的人。中大的体育课程一年级是普通体育,二年级以后可选篮球,排球,体操等类。选太极拳一度成为风尚,但学太极拳往往得起早,同时考试时须单独表演,一学期之后,废然而退的不少。
学校每年举行运动会,此外还有院际或公开的各种球赛。在沙磁区,各种球赛或田径赛没有能够和中大争衡的学校。
生活上,中大师生都表现的非常简朴。在重庆时,同学每人都有学校发给草绿色军服一套、深灰色棉衣一件作为学校制服,这些服装被称为“荣誉制服”,不分男女,都愿意披在肩上。到了南京,这“荣誉制服”仍不时出现,但已经没有在沙坪坝的普遍了。若干时间后,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少,往往会被新生误认为是工友闹出笑话,后来就无人再穿了。但是在学校里,西装革履,油头粉脸的人绝少。复员回到南京百废待兴,学校食堂又是公费,伙食自然也不会很好。学生自治会办有辅食部,价钱比市上便宜,质量一般。学校供给体格较差的同学每日鲜牛乳,当可稍补营养的不足。中大学生普遍的穷,但全校崇尚着一种简朴笃实的作风。
抗战时期内迁西北或西南的各大专院校由于战时环境的影响,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而重庆沙坪坝的中大校风学风尤为艰苦勤奋。当时曾流传着对各地大学生概括的评说:“洋里洋气的华西坝,土里土气的古城坝,土洋结合的夏坝,艰苦朴素的沙坪坝。”这种分类虽不太确切,但也道出了中大所在的沙坪坝的确是比较艰苦朴素而又充满活力的,它充分概括出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学习面貌和沙磁文化区欣欣向荣的特点。
中大图书馆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之一,图书馆中外藏书五十余万册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全部完整地西迁重庆,这一点中大是得天独厚非常幸运的。修建在松林坡顶的不足一千平方米 的图书馆是一座简易的平房,只能容纳500个座位,而学生人数超过座位数倍,图书馆里整日整夜都是挤得满满的。每一个人都在埋首书案,在忙着看书,做练习、做报告。图书馆虽然已经一再地扩充,还是容不下大量的需求。座位僧多粥少,因此在中大学生占座位、抢图书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由于教室、图书馆和自修室有限,许多学生便选择在茶馆学习,故茶馆也成为学生的学习场所。沙磁文化区各个大学校园里,均设有一种专以调节学生生活的学生茶馆。一年四季,生意兴隆。重庆沙坪坝是带有乡村风味的市集,但是却因为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成为了战时新文化的重地,成为了最平民化的新学府。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整齐划一的油漆书桌,也没有现代化的各种新设备。校舍好比营房,饭厅就是礼堂,全校都居住在一所大山上,没有平地出门就要爬山。但是物资的设备虽然简陋再简陋,全校师生的精神却很振奋,他们不仅乐观向上,而且在内心有着明确的民族使命感。他们过着一种紧张严肃又不乏活泼的学校生活,等待着抗战的胜利,等待着全校复员凯旋还都的那一天。
战时的中大也崇尚着一种自由的作风,在沙坪坝、松林坡上有闻名的民主墙,墙上每个人可尽量讲出他心里要讲的话,签上姓名或学号,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轰轰烈烈的大运动由此发剙。紧张的时候,满墙都是白纸黑字,又加上许多红圈,学校里许多设施的改善就是本此意见。这垛墙,象征着整个学校的动静,是中大的“晴雨表”,校方和同学都很重视民主墙上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到了南京,学校的校区相当拥挤。但是无论是四牌楼还是丁家桥,“民主墙”依旧是校区必不可少的标准配置。学生们有了自由发挥的阵地,但是大部分学生关心的还是学校的大事,如校长的去留、宿舍生活的改善、少数党派的奢适。社会政治问题也在忧国忧民的同学们关切之中,如国民大会的进展、联合国的会议、战后世界政治的重新划分,除此之外,民主墙上自然也少不了红红绿绿的布告。校区宿舍竣工后,其分配方案原先没有安排女生,引发女生的强烈不满,要求与男生同等待遇,男生也异口同声帮助声援。训导处不得不改变初衷,将女生安排入文昌桥第六宿舍,相邻男女生皆大欢喜纷纷庆贺。即便是一只手套的丢失寻找,也以“找配偶”之醒目标题引发同学纷纷驻足。可见民主墙的魔力不可小觑。虽然四牌楼和丁家桥都是在市中心商业区附近,学生业余时间可去的去处多了很多,在学校的业余时间相应少了。但是中央大学的师生对于国家政治的变革,对于校园生活各方面的关切,比起相对闭塞的重庆沙坪坝要敏感更多了。

国立中央大学校园(重庆沙坪坝1937 —1946)
社交活动在中大是比较保守的。重庆毕竟是抗战时期,各方面学习和生活都比较简朴。男女同学间来往较少,女生宿舍都挂上【男宾止步】的牌子。到了南京,随着国家机关和大学等机构的复员,社会生活逐渐恢复,男女同学之间的联系也便利了很多。复员后的中大校内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以学生自治会为推动中心,学术上的讲演会,座谈会和同乡、同学会的活动每周都有,星期天的名人学者演讲多至一日数起。学生往往一人有好几个“会籍”,最少也得有毕业母校的校友会、出生地的同乡会和所在系的系会三个会籍,如果再参加其他各种学会“会籍”更多,到了南京,一切还未上正规,没有什么活动。
中大学生虽然在学习上毫不放松,在社团活动方面,中大同学一贯也是不亚于任何学校的。白雪国乐社是有历史的社团,他们定时练习,每次演奏都博得不少好评。外文系的译文社,更是课外辅助了课内,他们的大幅壁报,每期都吸引了大批的师生。艺术系的野马社,绘制漫画,水准绝不低于任何报纸或杂志的漫画;青年会每年暑期都举办夏令会,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是每个中大同学都熟悉的。但是有些社团限于经济困难,活动受了限制,例如在沙坪坝时中大同学主办的“大学新闻”到京以后休刊了,中大评剧社也多时没有登台了。
根据教育部的公布的改进师范学院教育办法,复员回到南京后的中大师范学院,只保留了教育系、体育系、教育研究所等。其原有的国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和博物系,一律改为归并到各文理学院授课不再单独设系。原由中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招收的学生,也全部转移到地理系继续完成学业。
一九四六年,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以后,大部分系都开始招收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教育部拟定的《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大学各研究所应与各学系打成一片并依学系名称称为某某研究所,大学各研究所设所主任一人由有关学系系主任兼任。原先的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和相应的研究所学部等均予以废止,各研究所学部改称为研究所,由各系主任兼任研究所主任,人员配备相同但是另有经费来源。如原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也改称为地理研究所。一九四四年末从地理系独立出来的气象系原先没有成立学部,此时的研究功能也由地理研究所包容在内,以地理研究所气象组的名义进行研究工作。因原地理学部主任胡焕庸教授和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都在美国考察研究,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研究所的主任由在李旭旦主任外访期间担任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锷教授兼任。一九四七年秋,李旭旦教授从美国访问研究结束回到中央大学地理系,重新担任了地理系主任,也兼任了地理研究所的主任。

国立中央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大礼堂,1931年建成
一九四O年四月,汪伪政府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了自己的伪“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统一称为“南京中央大学”),任命汪伪“教育部”政务次长樊仲云任校长。陆续设有文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至一九四四年,前后招生940人。与此同时,其他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也有部分伪政府“移用”原国立大学校名的大学陆续开张。部分流落在沦陷区的教授和青年学生,进入了这些与原国立大学校名相同的“伪”校工作和学习。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根据教育部对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工作的训令,汪伪政府利用金陵大学原址开办的伪“南京中央大学”停办解散,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单位协商进行。后商定“南京中央大学”的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归金陵大学。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和《设置临时大学补习班办法》。各地政府教育部门应对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及毕业生进行甄审,在校生进行补习。
南京临时大学设在汉口路金陵大学校址内。南京中央大学的文、法商、教育、理工学院一、二年级,农学院及医学院学生按原在班级,分配到南京临时大学各院系学习。理工学院三、四年级学生,以南京师资不足为由,分配到上海临时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一九四六年六月,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者,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位。教育部以国立大学的相同标准为各地临时大学的学生编印了毕业纪念刊。南京临时大学的《国立南京临时大学毕业纪念刊》,教育部长朱家骅题写了“文会辅仁”四个大字作为标题。内容包括教授通讯录(181位)、职员通讯录(84位)、毕业生通讯录(311位)、各年级学生通讯录(1717位)、毕业照片,临时大学同学会编后:勉我同学等,共计73页。
临时大学各地未毕业的学生按照所在学院系与地区,分配到规定的学校继续学业。南京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分别分配到中央大学、安徽大学、交通大学、江苏医学院等校继续学习。在上海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原“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土木系和机电系学生大都留在交通大学,少数转入中央大学;化工系学生则分散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由临时大学分发到中央大学的原“南京中央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就成为复员后中央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到青年学生的学业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沦陷区以内的这些肄业生、毕业生,通过甄审和临时大学补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社会虽然有争议,但是在清理沦陷区的教育问题方面,特别是考虑到尽量支持青年学生完成学业。在各战时迁往大后方的国立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返回收复区原址之前,全国解决了汪伪政府遗留下来的大学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近万人,这部分青年学生后来大都通过再学习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和复员回迁的各大学学生一起,成为战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以整建制在南京校区开学为标志,西迁陪都重庆九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正常办学。此后随着内战的爆发,中央大学仅仅在南京坚持了两年半,就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校名也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一九五○年十月又改为“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起到一九五三年底,教育部全盘学习苏联高校设置的模式,理工分家,文理分家,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迁移到天津路原金陵大学校址,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学,工学院则留在原中大四牌楼校园以南京工学院的新名称独立办学。其他如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的水利系、航空系、农学院的森林系等,均各自独立建校或合并他校相关专业再造江山。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校档案,则由重组后的南京大学持有。现在这批反映到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的6881卷档案,保管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自上世纪初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起,几代优秀学人辛苦耕耘建成的中国声誉最高的综合性国立大学,从此以开枝散叶的方式走入历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说明:为以示区别,本文所述的“中央大学”或“中大”,均指位于南京四牌楼和丁家桥或重庆沙坪坝,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中央大学”,以“南京中央大学”指汪伪政府在南京举办的伪“国立中央大学”。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文學檔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