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培义
一九七八年,那是一个秋天。
就大自然而言,那个秋天似乎与以往的秋天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那个秋天又的确与别的秋天不太一样。
在北京,有一位老人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开春就到祖国的南海边画上一个圈;在祖国各地,许多家庭的家长也在收拾行装,当然不是想去哪儿画圈,而是准备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大学。
这许多家庭中,也包括我家。因为那一年,我以高出体检线将近90分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工学院。那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次考试。
一
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这不仅意味着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变,而且做父母的脸上也极有光彩。所以,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父母亲连日里大摆宴席,遍请亲友。然后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箱子作为行囊,高高兴兴地把我送上了火车。印象里,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的父母亲,好多年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火车到达南京的时候正值深夜。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座六朝古都的地面。走出站台,望着古城灿若繁星的灯火和夜色中依然熙攘的人流,恍然如梦。这就是雕栏玉砌的金陵吗?这就是虎踞龙蟠的南京吗?
激动和好奇转瞬即逝,四年的南工生活开始了。
二
“南工”是南京工学院的简称(如今复更名为“东南大学”,但是我习惯地把母校简称为南工),那是一所大师云集的学校。对南工的很多记忆,因为有了大师的加入而变得饶有趣味。比如,当身兼江苏省副省长的建筑大师杨廷宝与我们一起挤在学校的公告栏前看公告时,我就在心里得意洋洋地想:哈哈,原来我和大师的距离这么近!再比如,当身兼省人大副主任的土木大师刘树勋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脖子上挂一副中药,颤颤巍巍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暗暗感叹:岁月常青,但大师老矣!

老去的大师是学校的灯塔,给我们领航的,则是那些授课的中青年老师们。
教我们《普通物理》的恽瑛教授,其实不算年轻,那时她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私底下,许多学生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恽老师是当时学校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讲课的时候风度翩翩,激情飞扬,语速很快,板书也很快,而且汉语和英语掺杂。深奥的大学物理让恽老师讲得通俗易懂,听她讲课时,总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畅快之感。恽老师的课非常受大家欢迎,只要有她的课,不但外系的学生早早地就来占位,而且许多年轻的教师也纷纷前来旁听,有时简直就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
与恽老师相比,教我们《高等数学》的韦博成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韦老师讲课时,语速不徐不疾,节奏不紧不慢,思路相当清晰,显示出数学家才有的那种严谨。他的板书,就像是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给人以美感。有时遇到大段的推论,他的板书就写满了整个黑板,只留一块空白的地方没写。不知为何,此时我就想起“有板有眼”这个毫不搭界的成语。待到整个黑板写完,结论也就出来了,那结论正好就写在那块空白的地方。这时全班的同学就笑了,原来那“眼”是他专门留在那里,用来“画龙点晴”的。一堂枯燥的数学课让韦老师上得如此生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力使然。
韦老师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他的板书,而是他对课堂的把握。当他把一节课的所有内容讲完,然后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不出十秒钟,下课铃准会响起。不像给我们讲理论力学的那位老师,当下一节课的上课铃都响了,别的老师已经等在门口,他还在讲台上津津有味地讲他的“二力杆”。
三
那时,上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之后,所有的同学都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教室,冲向食堂。
同学们那么急切地冲向食堂,不是因为南工的食堂办得好,而是因为去晚了就要排很长的队。另外,也可能是因为食堂的油水太少,学生饿得太快。用《水浒传》中李逵同志的那句话说,“嘴里能淡出鸟来。”
那个年代,同学们除了对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对肉的渴求也同样强烈。如果食堂打菜的师傅给哪位同学多打了几片肉,那同学准会在心里涌起一种亲人般的温暖。南工的学生食堂,不但菜里面肉片稀少,而且口感很差,于是,一些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就到学校大门旁边的阳春面馆去吃肉丝面,估计那家面馆老板的心里非常感激南工食堂的师傅。
吃完午饭就回到宿舍午休。我们的宿舍十来平方米,住着八名学生,基本上都属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种类型。平日的生活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专注学习心无旁骛,不像现在的学生生活那么丰富。
因为不太关心外界的事物,所以有时也闹点小笑话。一天午休的时候,有位弟兄非常气愤地拍起了桌子:
“这英国人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了?”大家被他的突然之举吓了一跳。
“你看你看!”这位仁兄拿张报纸给大家看,“咱们的主席到英国访问,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来迎接,他撒切尔自己不出面,派他的夫人迎接咱们主席,这不是小瞧人吗?”
全宿舍的人哄堂大笑。连大名鼎鼎的撒切尔夫人都不知道,这大学上的!笑过之后才告诉他,撒切尔夫人就是英国首相啊!
四
当然,我们宿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闭门死读。睡在我上铺的那位兄弟,就喜欢开门办学。这位兄弟叫章勇,江苏丰县人。章勇是我们全班最聪明的学生,也是高考时全班分数最高的学生,他的分数比体检线高出一百多分,高于当年北大清华的录取线。
章勇是执著的电影迷。当别的同学把课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的时候,他却流连于南京各大影院的门前,手里拿着两角钱,等着买别人的退票。除了迷电影,章勇还迷足球。有一年,中国足球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连续赢了几场,形势大好。这点燃了许多学子的激情,那段时间章勇整日沉浸在足球的世界里。接下来的一场,中国队又以3:0力克西亚劲旅科威特。眼看着冲出亚洲的梦想就要实现,章勇兴奋得如同猴子上树一般,摸出个脸盆当铜锣,与一大帮和他同样痴迷足球的同学一起,连夜上街庆祝。庆祝的队伍一直来到省政府,结果把省政府的卫兵吓了一跳,将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又叫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闹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大学生们在为中国足球队庆祝呢!
由于是同乡,又是上下铺,所以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和章勇的关系最为要好。他有什么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向我透露。大三暑假返校的时候,他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一边,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是他与一个清秀女孩的合影。他告诉我,那女孩是小黄姑娘,亲戚给他们介绍的,现正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望着满脸幸福的章勇,我知道,这兄弟已坠入爱河。
五
章勇小我一岁。他都在爱河里游泳了,我还是形单影只,心中不免失落。其实我也有自己心仪的女孩。那女孩在我到南工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皮肤白皙,面容姣好,身穿那个时代常见的蓝上衣、黄军装裤子,朴素而文静。
我几乎是在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上她了,但一直没弄清楚她喜不喜欢我。那个时候,男生和女生的交往还是很拘谨的,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所以每次单独与那女孩在一起时,只会心跳加速,却不敢让她知道我对她的喜欢。
大二那年,南工因为扩招要盖沙塘园宿舍。由于工期很紧,学校就动员全体学生到建筑工地帮助劳动。男生帮着运砖和水泥,女生则做一些端茶送水之类的辅助性工作。正是炎热的初夏季节,同学们挥汗如雨。这时,那女孩端着碗开水来到我跟前:
“天太热,喝点水吧!”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没心没肺地回答:
“我不渴,干这点活算什么!”
女孩走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虽然错失了机会,但心里始终有她的倩影。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表白,只好一个人在心里忧伤地唱: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姑娘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她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
这首歌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唱,忧伤也就一次一次地缠绕着我,但始终没有勇气向那女孩表白爱情。直到大三,鼓足勇气准备向她示爱的时候,另一个小子已经捷足先登了。我只能化悲痛为无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二人出双入对。

(南京工学院84781班全体同学毕业合影)
唱完“红莓花儿开”,接着就唱起了“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因为毕业的时刻已经来临。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怀着几分期待,几许惆怅,我站在四牌楼二号的大门前,向四年的南工生活挥手作别。
六
毕业之后,同学们劳燕分飞,在许多年里我与班里的多数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与章勇是个例外,因为我们俩同时被兰州军区招收入伍,不久,又一起到军区装甲兵教导大队担任文化教员。两个南工的上下铺兄弟在西北的大漠又成了同事加战友,很是欣喜。后来,章勇被抽调到西安陆军指挥学院,十多年后,他转业到西安的一家国家政策性银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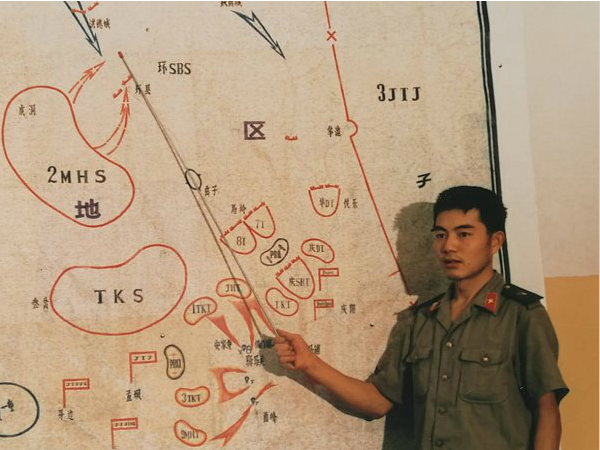
章勇转业的第二年我也从部队转业了。返乡途中路过西安,于是便下车去看望这位十多年未见的好兄弟。章勇夫妇在西安一家环境很好的饭店热情接待了我,这是我二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当年照片中那位清秀的女主角小黄姑娘。
当然如今已经不能称她为小黄姑娘了,因为她已成长为西北工业大学颇有造诣的一位教授。
友情伴着美酒在心中洋溢。
席间,我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在南工度过的青春时光,感慨万千。
那时的青涩,那时的张扬,那时的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成为我们心中长久的珍藏。
在遥远的西安,我们两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南工弟子一起为母校祝福。母校是什么?有人说,母校就是你一天骂她八遍,却不允许别人骂她的那个地方;我说,母校就是你既为她的悠久而自豪,又希望她永远年轻的那个地方;就是留下了你的青春和牵挂,让你远在天涯也魂牵梦萦的那个地方。
二〇一六年的冬天,南京下了一场雪。朋友圈里突然跳出了几张母校的雪景,大雪纷飞中,有一对年轻人在东大校园里拍婚纱照。

那是我们无法穿越回去的青春岁月。
当东大还叫南工的时候……
(作者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陀螺仪及导航仪器专业七八级校友,现在江苏省邳州市邳州广播电视台工作)


